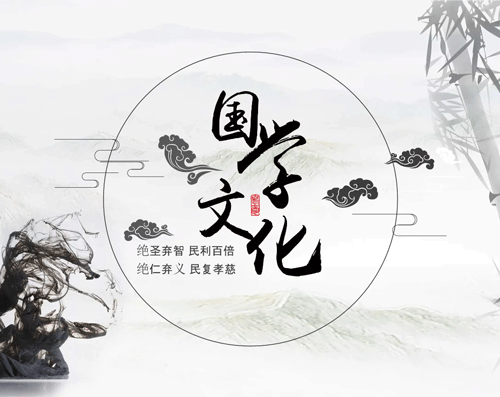鲁迅与佛教:饱尝“人生之苦”,生“厌离之心”
发布时间:2024-02-23 14:14:09作者:地藏网1923年,鲁迅,陷入了人生的第二次绝望。
生命、生存,全部的意义,就只剩下黑暗中的自己。他再次沉默了。这一次,他将自己放到了手术台上,拿着解剖刀亲自打开了自己的身体,不管此后是否能够重合。
1924年,鲁迅执笔《野草》,一直到1926年完成,幽深诡丽的画卷,一开始就这样子说到:"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
无数人发现,鲁迅,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种佛教的气质——
日人奥田杏花在鲁迅逝世之后,这样子描述对于鲁迅晚年的印象:"要是和鲁迅有一言之交,就会觉得他毫无人间的欲望:不论在金钱,在虚荣。若照佛法来说,同时已是遁入了"般若"之境的人了"
在先生唯一的一部散文诗集《野草》中,每一篇都是一个个漩涡汇聚成的大漩涡,让人应接不暇、艰于呼吸……像极了佛教所言的"缘生"与"缘灭"。
一部《野草》,所谓因缘结下的果
纵观鲁迅的一生中,从少年到中年,再由中年到暮年,总是留下佛教的背影——年少时候,为求平安,他自小就被父亲领着拜当地长庆寺的主持和尚龙师傅为师,赐法号长庚。青年在日本留学,学《说文解字》和《楚辞》于师章太炎,而此时章已转治佛学,鲁迅颇受影响提笔作《破恶声论》为佛教辩解,"夫佛教崇高,凡有识者所同可",怒斥那些"毁伽蓝为专务"的人。民国初隐没与绍兴会馆,开始大量阅读佛经,从1913年开始,日记中也出现大量购读和借阅佛典的记录,1994年购买数量竟占到了八成有余,确属惊人……
鲁迅的一生,不论得自长辈的呵护,抑或是年轻热血的草率,还是落寞时刻,佛学都在鲁迅生命的各个阶段留下的足迹,似雪地鸿爪,却又在茫茫中显得异常醒目刺眼。
回看1923年,7月19日,鲁迅收到周作人亲手递给他的一封绝交信,曾经誓言永不分离的手足就此失和,作为鲁迅人生最后的寄托,"兄弟之情"的破裂,若人生的天地裂开了一道大口子,不断坍塌,和着此前《新青年》杂志解散带来的作为笔者事业的虚无一起,化作了一片黑暗,吞没了鲁迅世界的所有星光。这个时期,鲁迅无疑是痛苦和不断挣扎的,在这个时期,他和佛教是走得最近的一次。
也正是如此,佛教的思想,早已在鲁迅的灵魂深处扎下了根,翻开《野草》处处可见大量的佛教语词:大欢喜、虚空、地狱……甚至《野草》的语式和节奏似乎也受到了佛经的影响,"递给人间,可以歌、可以哭,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出自《野草 淡淡的血痕中》)像极了《金刚般若波若蜜经》中""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
鲁迅并不是一个信仰佛教的人,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皈依佛教,但是佛教影响之大小,于鲁迅,于众人,于他的苦难有关,并不取决于信仰与否,或者说,此时佛教所种下的前因后果,和鲁迅的无法停止的天才的思想自觉一起,幻化做了一个"救命稻草",供他在苦闷的精神世界里玩味。
四圣谛:"集"为"苦","灭"为"道"
在佛教之中,苦,集,灭,道,作为释迦摩尼亲证的四种人生哲理,是佛教的基本道义——知"苦"而断"集",断"集"以离"苦",为声闻乘厌离世间的观行。"灭"为"道"的收获,此二谛为超出世间的因果。
佛家以"苦"为第一谛,以个人感受出发点,切近人生、自我。人生无不在"苦"中,世人有生在苦中不知"苦",至此无缘,或者以想"脱苦"而不知"苦"之因,终无缘或不得解脱之道。

鲁迅的厌离,是对于自我,他就是苦,苦就是他,在《野草》的诗篇中,他开始品味自己,就像是一个面容冷漠的人品味一杯酒,所不同的是,他品尝到的,不是甘中有苦,而是在漫无尽的苦涩中寻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甘甜。鲁迅,他早已深感到自己人生的痛苦,欲脱之后快,纠缠在此以情景之中,也由此达到了人生的精神谷底:失去了一切,未来的一片黑暗。就像是他自己说地那样子:"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于是,在散文诗篇中体味到自己的痛苦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又是如何面对这一终极命题。
此时的鲁迅已经身力憔悴,《影的告别》中的"告别",《希望》中的"希望",《过客》的不堪回首,都是对于自己极度的厌恶,在这个过程之中,他让一个自我看着另一个自我缓慢死亡,亦然无异于自虐。所以,在自我厌弃的长期矛盾中的犹疑惶惑中,他希望自己做一次最终的抉择。
《野草》的解脱之道:"自我"与"无我"的殊途
鲁迅终究不是一个佛教的信徒。
在《野草》的书写中,他不是直接皈依三宝,以达涅槃,而是自我怀疑、自我挣扎、自我探寻、自我征求,走了一条自我见证之路。就像是千百年前的项羽,带着万千人马破釜沉舟,再无退路,像司马迁在幽幽的黑夜里,只为著书无所顾虑的闪烁的眸子,他最终将那个自我厌弃的自己交给另一个自己——那个虐待着自己的自己——在精神的手术台上,肆意解剖,不管此后能否再次重合。
佛教,讲究缘起缘灭,所有的一切,只为最终发现"真正的自我"并不存在,获得一个超脱。然而鲁迅不是,他面对自己一个又一个人生的漩涡,不顾一切的前往,将自己所执着的一切,层层分解下去,最后归为空无自性,最终抵达自我的不存在之后,而是走了一条自我体验、自我见证之路,回到了生存的人间。
他是向死而生的——
向死:从《影子的告别》写下的临行绝笔,到经历"诚与爱"的荒漠的《求乞者》,再到被异化的复仇的《复仇》,最终获得的最后收获的《复仇(其二)》,然后到对于《希望》的三度询问,再到魂之舞的《雪》,最终迎来了《好的故事》的美好的打破,在身为《过客》的路途中迎来的峰回路转。
死于生的挣扎:在《死火》中的苏醒,在《墓碑文》中对自己过去的审视,在《失掉的好地狱》《颓败线的颤抖》对现实审视,最终在《死后》获得了新生。
于是《从这样子的战士》到《一觉》,他又重新开始了战斗。
如果说,鲁迅是一诗人,那么,他一定是虔诚的,如果说,鲁迅是一个战士,那么。他一定是慈悲的,若果说,鲁迅是一个佛陀,那一定不是正确的。鲁迅的事业,在人间。但是,鲁迅在和佛家的因果轮回之间,有着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