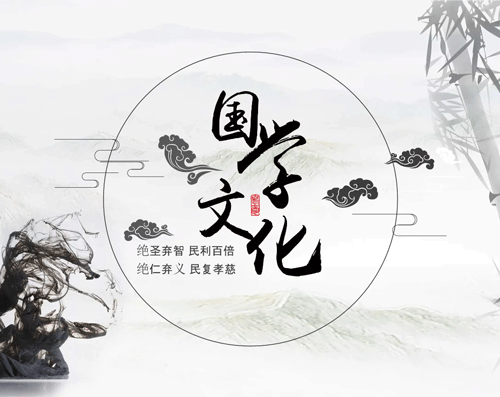论佛教伦理的中国化
发布时间:2023-07-19 10:19:19作者:地藏网一
我们常用佛教伦理儒家化来形容佛教伦理中国化。在我看来,佛教伦理儒家化只是佛教伦理政治化的结果。佛教传入中国后,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首先必须政治化,这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所决定的。
佛教是从印度传入我国的。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从人生和世间“一切皆苦”的基本观点出发,以追求超凡脱俗和无差别的平等、不念尘世、远离政治的超现实的涅槃境界为最高理想,对人生采取出世的态度。尽管佛教也有其不尽然的地方,如在部派佛教时期,上座部的《毗尼母经》就明确提出了佛法和王法“二法不可违”,主张佛法要服从王法;大乘佛教兴起以后,其中观学派的奠基人龙树深得当时甘王的支持,曾作《宝行王正论》和《劝戒王颂》,专门对甘王讲述如何治理国家,对待臣民。但就其主流来讲,避世、厌世和出世是佛教的基本特征。大家知道,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是与农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等级宗法制度,这种基于同族的血缘、同乡的地缘而建立的父家长制决定了家族伦理即是社会伦理、国家伦理。这样,“孝亲”成为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本位,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夫孝,德之本也。”(《孝经》)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加之父家长制表现在国家关系上就是中央集权的君权专制主义制度,因而“孝亲”与“忠君”是息息相通的。正是与父家长制的宗法制度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制度相适应,鼓吹“孝亲”和“忠君”的“三纲五常”成了儒家伦理的基本道德规范,儒家伦理也由此在中国封建社会获得了无以伦比的强大生命力。由此可见,被人视为“无君无父”的佛教伦理,在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构成了极大冲突。佛教如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就必须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相适应。这就是说,不念尘世,远离政治,对人生采取出世态度的佛教伦理,必须首先转化成为顾念尘世,接近政治,对人生采取入世态度的伦理,即转向“孝亲”和“忠君”,或者说至少通过种种手段和采取多种方式,力图说明佛教伦理与“孝亲”、“忠君”的不矛盾性,这即是佛教伦理的政治化。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佛教伦理的政治化是佛教伦理中国化的第一个重要途径。
佛教自东晋以来开始盛行,自此佛教与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关系日益密切,成为统治阶级实行封建统治的补充工具,这是佛教伦理政治化的基础和重要前提。

正如前面所述,“孝亲”是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本位,“孝亲”问题解决了,“忠君”也就迎刃而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孝亲观的形成,也是佛教伦理政治化的形成。事实也正是这样,佛教的政治化是与佛教亲观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当然佛教孝亲观在中国的形成也是极其艰难的,一个是削发为僧、谢世高隐、离家背亲出世伦理,一个是立身行道、忠君孝亲、齐国治国的入世伦理,它们之间的相互融通决非易事,而由中国封建社会的国情所决定,佛教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其伦理由“出世”向“入世”的转化又势在所迫。佛教进入中国后,面对“不孝”的挑战和责难,主要采取了迎合中国封建伦理的手段来寻求与中国封建政治的契合。一是运用“衍生”的办法,对印度佛教加以引申、演义,以证明佛教本来就讲“孝”。二是编造重孝的“伪经”,对孝进行渲染。如《大正藏》85卷载《佛说父母恩重经》即以宣扬孝道为主题,它说:“佛言,人生在世,父母为亲,非父不生,非母不育,是以寄托母胎怀身十月,岁满月充,母子俱显生堕草上。……饥时须食,非母不哺。渴时须饮,非母之乳。……呜呼慈母,云何可报?”这种以佛的口吻宣扬孝道,以世俗的眼光说明尽孝道的必要性的方式,增加了民众对佛的亲近感,加强了世俗伦理的信仰力量。三是通过会通儒家伦理思想来阐发孝道,以把孝抬到最高德行的方式,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孝亲观。汉魏时期《牟子理惑论》用“苟有大德不拘于小”的理由,首先在孝道上为佛教作为周全而机智的辩解,为往后中国佛教的“大孝”说埋下了伏笔。针对“佛教有违孝道”的指责,牟子引用儒典中孔子称赞泰伯、许由、伯夷叔齐的故事,说明孝道重质不重形,泰伯文身断发,许由逃入深山,伯夷叔齐离国出走,表面上看这种行为是不仁不孝,但实际上是大德大孝,同样,沙门出家修道,也是仁孝之举。东晋名僧慧远认为,佛法与名教形异而实同,出家求志,变俗求道,高尚其迹,悟佛全德,则能“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沙门不敬王者论》,见《弘明集》崐卷五)。即佛法能在更高层次上尽守忠孝,与儒家伦理殊途同归。到了隋唐时代,面对以傅奕为代表的反佛者的责难,以法琳为代表的护法者在佛教孝亲观的问题上进行了初步系统化的阐述。他认为,“广仁弘济”的佛教不仅与儒家伦理纲常并行不悖,而且其孝高出儒道两家,是“不匮之道”,能行“大孝”。至于宋代,“明教大师”契嵩完全以一个受熏于儒学的禅僧眼光,在其所著的《孝论》里,宣扬佛教最为尊孝,并以孝为戒,戒即孝的独特方式,最大限度地调和了与儒家伦理的矛盾,这标志着中国佛教孝亲观系统化的完成。
在佛教伦理政治化的过程中,“忠君”问题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家、思想家们争论和关注的焦点,这集中表现在“沙门应否敬王者”之争。东晋成帝时,庾冰代成帝诏令“沙门应尽敬王者”,指责僧人蔑弃忠孝,伤治害政,但尚书何充等人表示异议,与之论争。安帝时太尉桓玄又重申沙门应敬王者,并写信给王谧反复辩论,结果一批朝贵群起而攻之。慧远曾作《沙门不敬王者论》,作调和性的反对。而南朝宋孝武帝则下令必须对皇帝跪拜,否则就“鞭颜皴面而斩之”(《广弘明集》卷六《叙列代王臣滞惑解》)。到了唐初,“沙门应否敬王者”之争再度兴起,如唐高宗下令沙门应向君主和双亲礼拜,后因道宣等人反抗,改为只拜父母。但到中唐时沙门上疏的自称就由“贫道”、“沙门”改为“臣”了。元代重编的《敕修百丈清规》,更是先颂祷拜君主的“祝厘章”和“报恩章”,而后才是供养佛祖的“报本章”和尊崇禅宗祖师的“尊祖章”,这也标志着对这一问题的争论的永远结束和佛教伦理政治化的完成。
二
佛教伦理的补充性,就是佛教伦理对儒家伦理的补充。正是在对儒家伦理的补充中,佛教伦理找到了自己在中国生存和立足的空间,并以与儒、道两家合流和最终形成宋明理学的方式实现了佛教伦理的中国化。因而佛教伦理的补充性,是佛教伦理中国化的第二个重要途径。佛教伦理的补充性之所以能够实现,一是由于佛教伦理和儒家伦理具有同样的内在超越的特征;二是由于儒家“内圣”传统的中断,为佛教伦理对儒家伦理的弥补提供了现实可能。
教人如何做人,这是儒家的中心关怀和根本宗旨所在。儒家历来津津乐道的就是如何成为君子、贤人、圣人,强调在现实生命去实现人生理想,认为人生“安身立命之地”既不在死后,也不在彼岸,而是在自己的生命心中。如此,心性修养的内在超越变得至关重要,成为人能否达到理想境界的起点和关键。从《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其天”,到《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从《荀子》的“心者道之主宰”到《大学》“正心”、“诚意”,无不由尽心、见性以上达天道,由修心养性而转凡入圣。然而这种内心超越的人生哲学由于汉代经学的兴起一度中断。经学偏重“外王”而忽视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儒学“内圣”传统,强调的只是儒学中敬天法祖、经世致用的“外王”方面,实际上把“外王”的源流即“反身内求”的方面堵塞了。结果“外王”方面因无“内圣”之源丧失生命力。一方面,儒家被引向谶纬迷信和烦琐考证而失去了活力,“说五字之义,至于二三万言”(见《汉书》卷30《艺文志》第六册),以至于“崇仁义,愈致斯伪”(王弼《老子微旨略例》);另一方面,儒学伦理道德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的统治工具,在人们不再对之从“心”上下功夫的情况下,对一些统治者本身也失去了约束力,因而至东汉末年,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篇》引)的现象。这就造成了魏晋以后,儒学虽仍处官方正统地位,实际上从属于佛老之学。这种情况犹如韩愈所说:“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原道》)。
教人如何成佛,这是佛教的中心关怀和根本宗旨所在。所谓佛,就是觉悟者,即对人生和宇宙有了深切的体悟。在佛教看来,获得这种觉悟的根本途径,就在除去外在物欲的束缚,超越现实生活的牵累,消解内在的紧张,化除生活中的痛苦与烦恼,获得精神上的最大自由,自识真我,与梵为一。人人可以成佛,也与人皆可以为尧舜一样,其共同点都在培育理想的人格境界,造就人们高尚的内心世界,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就是“两家为说不同,然其所说内容为自己生命上的一种修养的学问则一也”。佛学与儒家的相同人生旨趣,为佛教在儒学“内圣”传统的中断之后在魏晋特别是隋唐时期兴盛起来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可以说,没有儒学“内圣”传统的中断,就很难有佛教在中国的兴盛。这主要在于,儒学“内圣”传统的中断,为佛教在中国找到了真正的地盘和归宿。这种归宿,就是北周道安在他的《二教论》中所提出的“释教为内,儒教为外”,也就是说,佛教于中国在“内”的方面大有开展的余地。佛教在“内圣”可以作为儒家的补充,这是连一些儒家学者也承认的事实。如柳宗元、刘禹锡认为,佛教的内美胜过外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儒家反佛名流韩愈、李翱在一面强烈排佛的同时,也一面羞羞答答、转弯抹角地承认甚至吸取佛教的心性学说。韩愈为儒家制造了一个从尧、舜、禹、周文王至孔孟及孟子之死“不得其传焉”的道统,本意是以此对抗佛教。但是,“道统”是模仿禅宗从释迦到慧能六祖的“以心传心”的法系事实,这从反面说明了他对禅宗“心法”的羡慕心理。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个人的正心诚意是修、治、齐、平的起点和基础。李翱认为孔子有“尽性命之道”的道,子思得了这个道作《中庸》传给孟子,孟子死后《中庸》所谈的“性命之源”就没有人传了。佛学则乘机抢走了这块地盘。这也是儒学之所以敌不过佛教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儒学要压倒佛教的唯一出路,就是重振儒学的心性传统,因而,在《复性书》里,李翱运用佛教的心性论及佛道的修养工夫,为儒家的“性善论”做了论证。考察宋明理学,我们不难发现,它的形成和建立正是以儒、佛、道的融合为基础的,或者说,正是有了高于佛教的心性之学,才有集中国传统思想之大成的宋明理学的诞生。
同时,正因为“内圣”是对儒学的补充,所以从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来看,那些历久弥新在中国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佛教流派,就是那些不同程度地向“心”内倾向的宗门。在天台宗的著述中,虽然他们常常以中道、实相说佛性,但最后又把诸法、实相归结为一念心,认为“心是诸法之本,心即是总也”(《法华玄义》卷一上,《大正藏》第33卷,第685页),并把能否成佛归结为是否觉悟和能否反观自心。与天台宗相比,华严宗佛性说的唯心色彩更浓。他们认为,一切万法乃至诸佛“总在众生心中,以离众生心无别佛德故”(《华严经探玄记》卷一),心佛与众生,是平等一体,相即相融。如果说天台、华严二宗把心具体化主要表现为一种倾向,那么,至禅宗首倡“即心即佛”,把一切归诸自心、自性,心的具体化就被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慧能伦理观的中心是佛性论,即认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郭朋《坛经对勘》)。“万法在自性”一语简洁明确地表达了慧能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在慧能那里,佛性成了佛的同义词,他要求人们“自说本心,自见本性”,“佛是性中作,莫自身外求”,由此他提出了“即心是佛”说。基于“见性成佛”的思想,慧能认为成佛只是一种见性功夫,即彻底认识自己的本性,因而他大胆破除传统佛教累世修行、会经布施的枷锁,提倡“顿悟”说,认为佛和众生的区别,就在于觉悟与否,而觉悟又在一念之差,“悟即无差别,不悟即长劫轮回。”“佛性”说和“顿悟”说构成了禅宗世俗化的基础。在慧能看来,世界上一切事物,人类的一切生活,都是佛性的体现,“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景德传灯录》卷六),“搬柴运水,无非佛事”,从入世见出世,在现实人世成就佛的正觉。禅宗在把佛教从天上拉到人间的同时,也就有效地弥补了儒家“内圣”传统中断后形成的空缺,从而实现了与儒家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