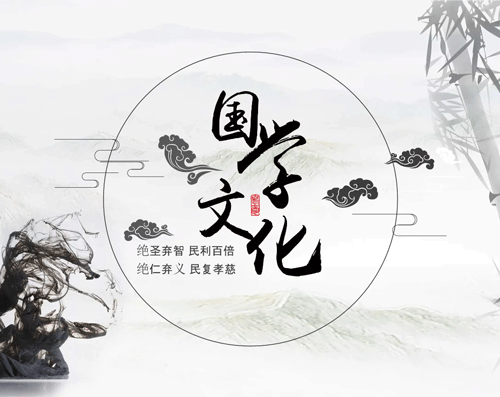近现代佛教文教弘法事业的开展
发布时间:2023-10-24 09:40:09作者:地藏网1、民间大规模刻经事业的兴起与发展
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佛教开始了复兴与革新的变化。佛教的复兴首先是在佛教传统刻经事业的大规模兴起。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宗教的传入,战争的摧毁和佛教内部发展到不依经典的末流,导致佛经被毁不计其数。一旦失去了经典,佛教将很快失去凝聚力,也难于同西方宗教相抗衡,佛教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志在复兴佛教的一些居士敏感洞察出这些威胁,出于爱国兴教的动机,他们展开了刻印佛经的事业。
杨文会认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普济众生”。1866年,杨文会与一批居士在南京“互相讨论佛学,深究宗教渊源”。1866年杨文会起草了《刻经章程》,首先创立刻字局于金陵。不久、郑学川于扬州创立了扬州藏经院,称江北刻经处。1875年,曹镜初在杨文会的帮助下创立了长沙刻经处。他们根据统一的刻经版本与校点体例,首先刻出了急需的常见经论,使佛教主要的宗派都有基本的依教经典。
杨文会一生主持金陵刻经处50年。郑学川后出家自号刻经僧,主持江北刻经处15年。他们共刻印佛经3千多卷,数百种,还有佛像数十种。中国佛教常用经论及主要的古德注疏,基本都有刻印。他们的刻经以效益高、质量精、有学术性及实用性等优点赢得教内外的普遍好评。
在杨文会居士等开创的民间刻经风气推动下,许多寺院恢复了刊刻佛经的传统,一些学者及民间书坊也自刻佛经。如敏曦法师在天台华顶寺刊刻佛经24种161卷。杭州昭庆寺慧空法师刻经数十种上百卷。1909年,宗仰法师在其女弟子罗迦陵的赞助下,出版了8416卷的《频伽藏》。浙江钱塘许氏、安徽吴坤也各刻经不少,还流通甚广。
刻经事业的兴起,是时代的需求,也是佛教复兴的开始。刻经事业为即将到来的佛学研究事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佛教各宗派的重新兴起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2、佛教文化的繁荣发展时期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最繁荣的时期。繁荣发展体现在刻经事业的空前盛大,佛教报刊发行激增,佛学教科书、工具书普遍流通,佛教图书馆、博物馆的建立及佛学研究、佛教文学兴盛这五个方面。
【刻经事业空前盛大】
以金陵、毗陵、京津刻经处为代表的刻经事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盛况空前。金陵刻经处由欧阳竟无继承之后,自1914年起,他致力于经籍的编校工作,在他的主持下,30年共刻佛典2千余卷。其中最大的成就当属继承杨文会遗志辑印的《藏要》。1927年,欧阳竟无集中各种力量收集多种经典版本,集国内的名家,从事《藏要》的校勘刻印。1929年起该书分册出版。已出版的有3辑50多种,其中第一辑就含经、律、论等共20余册。《藏要》的每一种书,欧阳竟无都亲自书作绪言,叙其源流与要旨。该书的精审无与伦比,就连日本也将《藏要》部分选为佛教大学的课本,可见其价值。
毗陵刻经处是冶开法师与他的弟子在清末创办的,自开刻至抗战前,以常州天宁寺一寺之力,共刻经775部,2469卷,卷佚之富甚至超过了金陵。1918年,徐蔚如、蒋维乔等创立北京刻经处,不久又创立天津刻经处,至抗战前共刻经佛经2千多卷,其中《四分律随机羯磨》一书,在弘一法师的校审下还成为国内律学的范本。天津刻经处刻出了大量华严学的经本,对复兴华严思想起到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同时从事佛经刻印的还有鼓山涌泉寺、杭州玛瑙寺、上海法藏寺等一些大中寺院。
除雕版印刷外,这一时期利用石印、铅印、影印等近代技术手段印刷经书的工程更为浩大。继《频伽藏》后,1923年,丁传坤、王一亭、梁启超、蔡元培、张誉等64人发起影印了日本的“卍”字《续藏》,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这部藏经收集自唐至清的中国佛教大德所撰论着1756部,7144卷,可补《大藏经》之缺。自商务的这次印行后,这部经在国内开始广为流通。
1930年西安卧龙寺、开元寺发现宋版藏经《碛沙藏》,1931年,叶恭绰、范成法师等组织发起影印,该藏共1532部,6362卷,装为593册。在筹印此经之时,佛教界又无意中在山西洪桐县广胜寺发现了金代的《赵城藏》,于是范成法师等主持选印其中罕见的佛典49部,组为120册,题名为《宋藏遗珍》,于1935年出版。《碛沙藏》与《赵城藏》的出版轰动一时,为佛教界及文化界的一大盛事。1932年,林森、太虚等朝野人士发起在南京中山陵兴起藏经楼,由南京政府拨出经费,影印《龙藏》十五部,供陵园的藏经楼与国内各大学的图书馆收藏。
【佛教报刊发行激增】
据统计,从1912年至1932年,中国佛教界有各种形式的大小佛教报刊3百多种,这些刊物短的数月,长的达几十年。其中狄保贤所创立的《佛学丛报》是佛教报刊的起步者,而坚持时间最长,发行面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要数《海潮音》。《海潮音》1918年10月开始发行,它由太虚大师创刊,中华书局印行。宗旨是“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海潮音》基本上是由太虚大师弟子与一些着名佛教学者主持,作者阵容强大,国内当时的一流佛教学者如章太炎、梁启超、欧阳竟无、汤用彤等,名僧圆瑛、仁山等都曾为它撰稿。它的内容不限于佛学,科学、哲学等各社会学科无不包含,在当时的读者中频有声誉,被称为中国佛教的《东方杂志》。当时太虚大师的重要佛教改革主张都是首先在该刊上发表的,该刊还对内呼应时代潮流,参与救国运动;对外呼吁反侵略,促进世界和平文化交流。它是近代佛教最具代表性的刊物。
支那内学院的《内学》年刊,是最富有学术价值的佛学刊物。它专门刊登国内佛学名家的研究成果。它反映出当时佛学研究的水准。1935年4月范古农在上海创刊的《佛教日报》是当时最通俗的佛教报刊,也是国内唯一的一份佛教日报。1930年上海佛学书局发行的《佛学半月刊》销量超过万册以上。1926年成都创刊的《佛教新闻》发行长达20年。较着名的佛教刊物还有谛闲、宝静创办的《弘法月刊》、《英文佛学季刊》、顾净缘创办的《威音》、常惺创办的《佛教评论》等,仅上海一地就有各种刊物20多种。当时凡是各地较大的佛教团体、佛学院都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就连社会上的许多报纸、电台也为佛教辟有副刊或专栏、节目,佛教的社会影响空前扩大。
【佛教书籍大量流通】
各地佛学院的兴起,需要大量的新式教科书与工具书,于是各种佛经讲义大量出现。较着名的有江味农的《金刚经讲义》,谢无量的《佛学大纲》,李圆净的《佛法导论》,常惺、蒋维乔及王恩洋各自的《佛法概论》,会泉的《佛学常识易知录》,史一如的《中华佛教史》、《印度六派哲学》,芝峰的《宗派源流》,张克诚的《印度哲学》等等。
工具书中以丁福保的《佛教大辞典》为最早,它收辞目3万多条,共300多万字,1922年上海医药书局出版。那时的工具书还有孙祖烈的《佛教小辞典》,高观庐、何子培的《实用佛学辞典》,梅光曦的《相宗纲要》,朱芾煌的《法相辞典》,熊十力的《佛家名相通释》,许地山的《佛藏子目引得》及陈海量的《在家学佛要典》等。
为了出版佛教经典,1929年上海佛教界创办了佛学书局,此后又创办大*轮书局,大雄书局等。其中上海佛学书局成绩最显着。他们编辑出版了《佛学小丛书》、《海潮音文库》、《佛学百科丛书》等,都有一定的规模。
全国寺院所设的法物流通处的职能在近代也有所改变,由过去以卖锡箔纸钱、香烛香炉为主转为了以流通佛经及佛教刊物为主,这对佛教文化的复兴与传播起了不小的作用。
【图书馆博物馆兴起】
在开办佛学院的同时,各地寺院也纷纷设立图书馆与博物馆,供应不同方面的读者借阅。开风气之先的是融熙法师于1920年创办的广州佛教阅经处。1922年叶恭绰、王一亭在上海设立上海法宝图书馆。范成法师于1930年在江苏如皋创立皋东僧伽图书馆。此外,各地佛教居士林也从创建初始就设立图书馆,对外开放。各地佛学院为便利教学,也多设有图书馆。规模最大的是武昌佛学院的经像图书馆,它于1932年被改组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它的藏书除佛教图书外,也包含一般图书,总计达到22428种,24230册,卷。世苑图书馆曾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学僧在此研修佛学。
【佛教文学及佛学研究】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广泛而源远流长,明清时期,随着佛教的衰落,佛教文学也惭呈枯萎。近代以来,各种领域革命呼声的兴起使佛教文学也有了新的发展。
清末时的苏、杭、湘等地,文人云集,雅士荟萃,且多与诗僧禅师交往,由此引得佛教僧俗也出现不少清丽洒脱的好诗。笠云法师被俞樾等推重,敬安法师与名士卢吟秋、贺师旦等人酬唱。敬安的诗还被收入日本编的《续藏经》,声名远播海外。
苏曼殊的一生很短暂,但是他创造出大量的佛教文学作品。他在佛教文学形式上多有创新,将弘扬佛教与革命思想渗透在字里行间,重建的光复会追认他与鲁迅并列为文化导师。他曾将多部西方反压迫的文学作品选译到中国,被誉为“独立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于中国的第一人”。他的诗多是反清爱国诗篇,慷慨激昂,有不少名句留传后世。他曾发表多篇小说,多以佛教故事为题材,倾倒无数青年读者。由于他的开创,佛教小说也与其它流派的小说一起并列在了近代文坛。居士之中,擅诗长文的也不少,如桂伯华、狄保贤就广负盛名。后者还曾开创中国近代第一份佛教报纸《佛学丛刊》,专门开辟文苑、杂俎、小说等栏目,为近代佛教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园地。
中国佛教向来有重视佛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近代佛教的复兴也带动了佛学研究的发展。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范围广,参与众,方法新。近代的佛教学术包括翻译、注疏、典籍整理、目录、辨伪、教史、辞书等多个方面。研究者不仅佛教信徒,普通学者也有,涌现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杨文会、太虚、弘一、印光、月霞、谛闲、汤用彤、熊十力、欧阳竟无、吕澂、丁福保、江味农等大量的僧俗佛教学者。佛学研究也不再局限于传统形式,许多人采用现代人文社科的方式和西方治学的方法,新旧的结合产生出为数不少的各种较高学术价值的着作,有些至今仍为佛教学术的顶尖研究。
近代佛教文教弘法事业的迅猛发展,为我国佛教事业的新生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提供一片新天地。
3、近代佛教教育的肇兴与发展
【佛教教育的肇兴】
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以佛道寺观充作学堂,清廷诏示军机处颁发各省付诸实施,由此触发第一次“庙产兴学”风潮。1901年,清政府明令各地置学堂,寺产开始受到侵夺。1906年,清政府两次允准办学,各地士绅乘机掠夺以肥私囊,在办学中侵吞贪污寺产难以计算,佛教处于存亡关头。对此,敬安法师上书抗议,章太炎与苏曼殊则于1907年发表《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告宰官白衣》的呼吁,启请清政府不要侵害佛教,呼唤佛教徒举办教育。
起初杭州白衣寺住持松风法师较早开设新式学堂,可惜被守旧势力谋害而未竟,继之湖南的素禅法师亦因力主办学被害。“庙产兴学”使佛教界内部改革呼声渐起,并于世纪之交开始自办新式教育。1903年,笠云终于在长沙开福寺办起了近代第一座新式僧学堂。1906年,文希也在扬州天宁寺创立了普通僧学堂。在清政府准许寺院自己办学后,各地新式佛教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07年,觉先法师在北京设立多所小学,僧俗兼收。1908年,敬安法师在宁波创办僧俗小学与民众小学各一所。1909年,谛闲与月霞在南京创设江苏僧师范学堂,尘空在河南信阳创办僧俗两等学校。1906年后,各地还纷纷建立僧教育会来联络筹资,共办教育。
辛亥革命前佛教教育的典范当数杨文会的祗洹精舍。杨文会一生倾心于佛教的新式教育。1895年,杨文会考察日本在南京开办的东文学堂,筹备培养弘法人才,1907年正式开办祗洹精舍。杨文会是筹划办学最早的人,办学思想也最为明确。他主张中国佛教必须跟上时代潮流,振兴佛学要兼习新法。他的学堂分为内外两班,外班以普通学为主,兼学佛学;佛教学堂仿世俗分为小学、中学、大学三等,不同阶段授以不同的教学内容。他提倡受僧教育者方可出家,不能学者则勒令还俗。他的思想为振兴中国佛教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奠基,对近代佛教教育影响深远。
杨文会把自己的主张贯注于祗洹精舍的教育工作。他因材施教,兼顾诸宗,并访延名师教导学生。在他不拘一格的带动下,学生各有所长。不过祗洹精舍仅收二十多个学生,不到两年因经费短缺而停办。虽然它的时间很短,但是所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成为日后佛教革新的先锋人物与中坚力量。
辛亥革命后,佛教教育在民国开国的新气象下也更上层楼。受到杨文会办学成功的启示,佛教界普遍明确了培养僧才的办学宗旨,新式教育遍地开花。自1912至1919年,浙江的海式于平湖报本寺、四明观堂、温州明因寺等地创办佛学研究社;摩尘于梵天寺创办性宗研究社。会泉于台湾台南大仙寺创办佛学院,于福建安溪龙山寺创办优昙初级学林;转初于漳州南山寺创办鹦鹉僧侣研究社、于南普陀创办旃檀学林;云果在泉州创办僧校。智光于江苏泰县创办儒释初等小学。空也于湖南衡山祝圣寺创立天台宗学校。道阶于北京尖源寺创办法师养成所。佛源于四川崇因寺创办六合学堂;昌圆于郫县金龙寺支持当地创办小学……其中最有名及最有成效的是月霞在上海哈同花园创办的华严大学。这个学校曾得宗仰、应慈等法师支持,收80多人。培养出戒尘、持松、慈舟、常惺等佛教后来的革新骨干力量。早期新式佛教教育的实践,为我国佛教事业注入了新生力量,也为大规模佛教教育的兴起积累了不少经验与教训。

【佛教教育的大发展】
近代中国“庙产兴学”之风从未止息,自1926年到1931年为第二次高潮。民国初期一部分人依然简单地认为佛教是迷信,指使或纵容军警冲击佛教。军阀冯玉祥信奉基督教,捣毁河南开封相国寺,没收寺产,造成全省大小寺院均遭抢劫。陕西、甘肃、江苏、四川、广东等地也有类似事件发生。1928年,南京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议没收寺产,改寺院为学校。中央大学邰爽秋发表《庙产兴学运动宣言》,同样主张毁佛兴学。1930年,他再次煽动排佛。1935年全国教育会议上,将全国寺产充作教育基金的提议被通过。这些举动使佛教界认识到,佛教唯一的自救之路就是尽快投入举办教育、文化的社会事业,服务社会挽救自我。
1918年,欧阳竟无筹办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继承杨文会的办学远见,并将大乘佛教的大悲精神与“五四”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主张“悲而后有学”,“救亡图存而有学”,要求学生为利他而学。内院于1922年在南京正式成立,设学事两科及学务、事务、编校流通三处。学科设有中学、大学、研究、游学等四级,各级又有不同科目的分类。学制相当成系统,是近代佛教教育的典范。
内院的大学、研究两部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以演讲、讨论、指导自习、研究为主,“教授以诱进阅藏,开启心思为鹄的”。这一方法比传统是一大进步,效果很好,培养出了汤用彤、熊十力等一代学术大师。姚伯年、梁启超、梁漱溟、陈铭枢等也先后来院深造。内院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维持时间最长的佛教研究机构,曾在院从事研究者达200多人,先后就读的学生数以千计,成为中国近代佛教研究的主要基地。
与内院交相辉映的是太虚大师创立的武昌佛学院。武院曾获得过湖北名流陈裕时、李隐尘等人的支持,由太虚大师任院长,梁启超任董事会董事长,开学时间比支那内学院还早些。1922年9月,内院招收首批学生80余人,设修学、随习二科(1924年改修学科为大学部),并设研究部,附设佛学女众部。课程有佛教史、西洋论理学、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生物学等,除了由太虚大师等僧人教授外,还骋请原北京大学教授数人。在学习外,学院还规定有一定的修持时间。武院以融贯中西,不拘宗派,戒学双修为特色。太虚大师概括武院的宗旨为:学术上注重打破旧宗派的固执成见,革新中国的佛教思想,吸收新思潮、新方法,以发扬中国佛学。在实践上,武院注重清净律仪,和谐合理,期望养成活泼健全的弘法僧才。武院是太虚大师革新的大本营,培养出大批的僧才,奠定了近代僧教育的基本方向。
继武昌佛学院之后最着名的是闽南佛学院。闽院创办于1925年,1927年太虚大师被举任院长,1930年设研究部。闽院是太虚大师佛教革新事业的第二个大本营,它对佛教教育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也曾提出了一系列的创见。闽院在太虚大师任职时期达到鼎盛。
武院及闽院培养的学僧散播全国,成为佛教革新的种子,由两院培养出来的师生所主持的寺院及佛学院遍布各地。如汉藏教理院,鼓山佛学院、岭东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普陀山佛学院、河南佛学院等。这些院校,成为近代佛教教育的中坚,也构成了佛教革新事业的骨架体系。自从这两院办学后,全国佛教界开始普遍响应。大、中寺院或单独、或参与办学,小寺院也有不少挂起了佛学社的牌子。形成了凡有佛教名山的地方必定有佛学院的现象,这使传统佛教教育不同程度的得到了更新。近代中国佛教之所以获得大发展,主要是由于太虚、欧阳竟无等在前面树立了佛学院的样板。
在第二次庙产兴学风潮中,佛教界办的社会教育也有所扩大展。早在二、三十年年代,较大的佛学院就附设小学,对社会开放招生。如武院附小,闽院附属的南山僧伽小学等,长春般若佛学院还附设中、小学、幼儿园各一所。各省佛教会及佛教团体也兴办起社会教育,如福建分会办了法海中学,九华山分会办九华平民小学,香港东莲觉苑办青山义学等。各寺院办社会教育就更多了,如常州天宁寺、泉州承天寺等均办有义务小学。台湾法华寺创办了佛教中学林,哈尔滨极乐寺创办佛教中学,甚至连接近塞外的陕北榆林也有了寺办小学。1928年,北平诸寺一下子就办了四所学校。个人办学的有,范古农创办的嘉兴商业学校、月河小学,俞嗣和、张兰亭在西安创办的济生小学、三育小学,施剑翘在苏州创办的从云小学等。
佛教界兴办的社会教育,大多数以失学青少年为主要对象,有的对孤儿提供免费食宿,有的对家庭困难的贫民子弟全免学费,有的干脆义务教学。这些学校一般以普通课程为主,佛学为辅。佛教社会教育面向社会的最下层,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的佛教教育还走进了了一些国立、私立大学的校园。如邓伯诚、许季平、梁漱溟、汤用彤、熊十力等先后在北京大学开设佛学课。蒋维乔在东南大学,唐大圆、张化声在武汉大学、梁启超在清华大学,王恩洋在成都大学等,都专门教授佛学。连着名学者如胡适、冯友兰、蒙文通、谢无量等也都将佛学写进了自己的哲学史、思想史等着作中,有的还作了相当高的评介。这与在华基督教所办的学校强迫实行基督教教育在无意中形成了一种鲜明对比。
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僧伽教育到社会教育,二、三十年代佛教教育为半殖民地环境下的民族文化别开一片新天地。